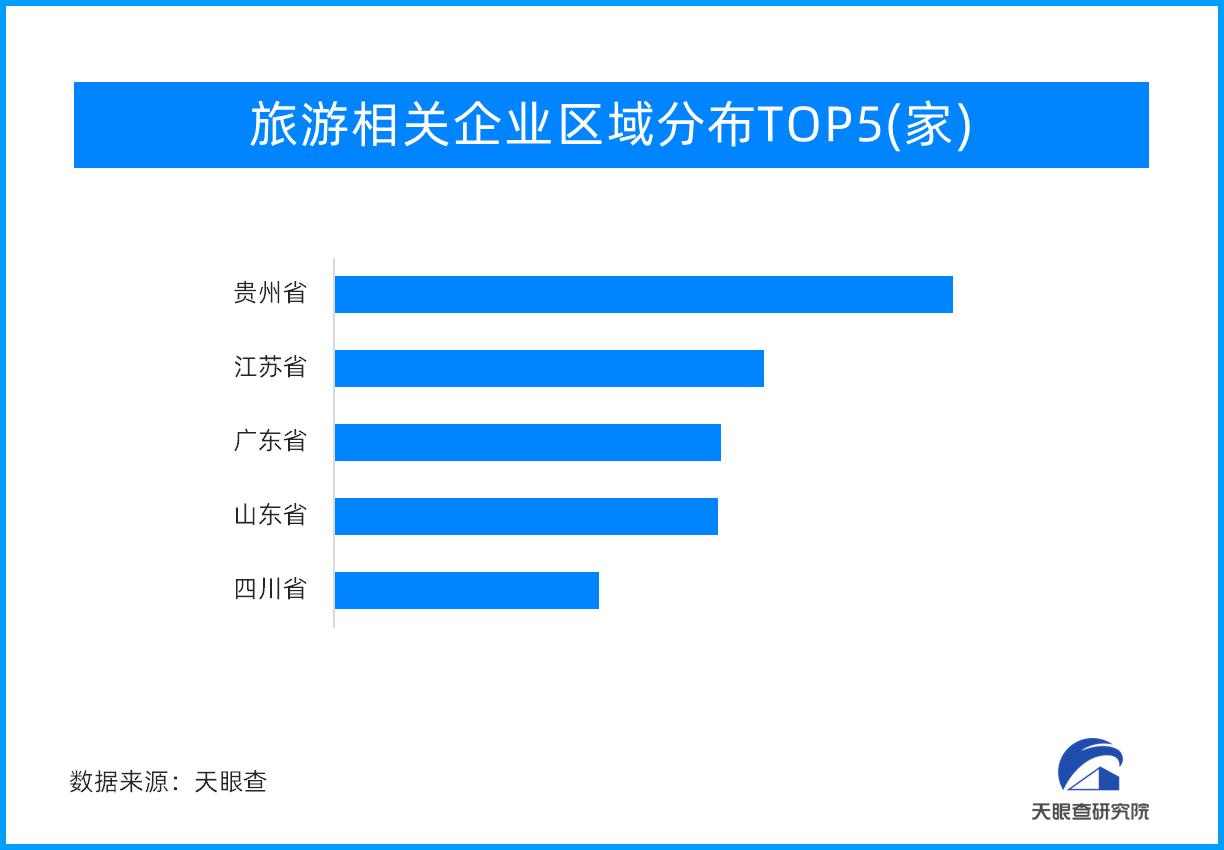盆窑黑陶传千载
我的故乡河南省沁阳市盆窑村,大概是中国少有的以产品命名,又以产品建村、兴村的村庄了。如今,很少有以古老的手工艺术而活色生香千余年的古村了。也许,从我的祖先们决定将他们的梦想置于太行山下这片沃土开始,便与黑陶签下了千年的契约。
丹河出太行陉进入平原的交汇处,向西约2公里处便是中国四大黑陶产地之一的盆窑村了。“小火既济而土合”,乌金墨玉是黑陶。明代科学家宋应星将黑陶写进了他的传世之作《天工开物》里。我们已无法想象是丹河岸边苍翠的竹林,还是太行山脚下上百座制陶作坊冒出的缕缕青烟,留驻了宋应星的脚步。也许是他想借这清雅的丹河水濯洗心尘?或是制陶祖先宁封子的后人做成的黑陶,勾起了科学家的心神,令他执念于此吧?总之,1000多年前上百家制陶作坊的窑烟,至今依然还在薪火相传……
一
黑陶是龙山文化中最引人注目的内容之一,源自人们日常生活的实物制品,其器物造型规整、单纯、直曲相关、圆纯相间、凸凹相衬、比例适中,因此又被称为中国工艺美术童年时期的一颗璀璨明珠。瓦陶制品一直与人们的生活息息相关,大至盛粮的陶瓮、陶缸,小至生活常用的陶盆、陶罐……
我的童年和少年时代,是伴着黑陶度过的。我们韩氏家族作为盆窑村五大姓氏之一,千百年来既是制陶历史的创造者,又是制陶工艺的传承者。年少的我曾亲眼目睹并参与过祖辈们如何找土、晒土、澄泥、盘泥、拉坯、烧陶……
制陶的工艺流程中,最费力的是澄泥和盘泥,技术含量最高的是拉坯和烧窑,最繁琐的是铣坯、压光和擦光。而最为壮观的场面应属装窑和烧窑的时候:晴天丽日之下,全村上百家作坊都将准备装窑的陶坯搬到窑顶,假如在空中俯瞰,盆窑村被一片土红色的陶坯覆盖着,在东西沟两条街道绿树的映衬下,犹如千万朵盛开的红花。傍晚点窑后,上百家窑顶冒起青烟直升云霄,与烧红的西天云霞相映成趣,一个时辰后,夜幕与窑烟融为一色。
而每每这个时候,是窑工们最幸福、也是最担心的时候。通红的窑火把他们疲惫的面庞映成古铜般凝重。他们喜的是这一窑即将出炉的黑陶带来的收入,而担心的是能否烧出理想的成品。制陶的最后一个流程尤为重要。烧陶的最好用柴是竹林的茎叶,因为这种燃柴产生的是“文火”。从大火到熄火的过程中,最后的熄火又最为关键。当窑工把最后的几把柴禾塞进炉膛后,其它帮工们在不到一分钟的时间内迅速把烧窑用黄泥封得严丝合缝,让弥漫在炉膛中的浓烟通过科学的渗透原理,使烟中的碳粒渗入到坯体而呈黑色。
二
盆窑村制陶的历史可上溯1000多年。据史料记载,最迟在唐代初年就已经初具规模。那时制陶工匠都是今盆窑村南的万善村人。唐代名将王世充、王茂元等都曾在此驻守。成千上万的兵卒马匹长期在这里安营扎寨,不仅把陶制品作为生活必需品,还把最好的黑陶作为贡品献于武则天。从那时起,万善的制陶业名声大震,迅速发展。
当年的盆窑村其实就是万善制陶人的作坊,盆窑人的根在万善。到宋代,盆窑村逐渐形成了建制的村落。黑陶的品种也由原来的轮制陶盆、陶瓮、陶罐等传统生活用品,增加上了套装的花盆、鱼缸、模印的鸟兽以及彩绘的花瓶等上百种瓦陶制品。盆窑村的制陶业发展至清代末年,一百余家的产品已经行销至山西、陕西、湖北、山东等周边省份,不少盆窑的工匠还纷纷在外省挖窑制陶。
水,是黑陶的血脉;土,是黑陶的骨肉。
制陶业之所以能在盆窑村兴起,跟太行山脚下这片特有的水土有关。南太行山脚下北纬35度这条纬线上,属于暖温带大陆性季风气候。北有太行山作为屏障,南有黄河的滋润,因一山一河的影响形成了这里光照充沛、气候温暖、四季分明、相对湿度较高的小气候区域。这种得天独厚的地理环境,为黑陶生产的主要原料红胶泥土和富含多种矿物质的水提供了保证。
红胶泥土大多深埋于山石之中或其它泥土之下,色泽油润,一旦历经浸泡过滤沉淀后,细如膏腻,再经过人工反复的摔、打、揉、搓后,弹柔似面团,捏胎时要求的纯度极高,大到如玉米粒的沙石,小到发丝都会使陶坯的质量受损。
其实,我们常说的黑陶是有关陶制品的笼统说法。真正学术意义上的黑陶,则是一个专用术语。盆窑村生产的“黑陶”,实际有黑、红、褐、白之分。真正的黑陶,必须套装烧制,即必须把即将烧成黑陶的器物套装进一个密不透气的容器里,并塞满优质的木屑刨花。祖传的秘方是以松木刨花为最佳,而用鸡蛋清做墨写在土坯上入窑,则会在黑陶上呈现金色的文字。
三
关于故乡,我有割舍不断的离情;关于黑陶,我有太多永远不会淡漠的记忆。
灵秀的山阳大地,因了山水的恩泽,自古传承着中华文明的因子,而且至今仍在闪烁着耀眼的光辉。自上个世纪末以来,故乡的黑陶在许多有识之士的努力之下,得以重新开发、挖掘、创新,完成了从实用功能到审美艺术功能的转换,让本来厚重的历史以“黑如漆、明如镜、薄似纸、硬如瓷”的形式,在世人面前展露新姿。古朴厚重的黑陶,展现了中国人原始的审美意识。那些浑然天成的造形以及那些只有在放大镜里才能细数的鲜活光纹,闪耀着我们祖先的智慧。
古老的丹河静默地流淌,我不知道那不舍昼夜的河水带走了多少岁月的时光,也不知道那潺缓的清流浣白了古今多少红颜鬓发,更不知道当年河里的船载走了多少盆窑的黑陶,送走了多少寒来暑往?而只有这千年古村以及太行山脚下那一块块苍桑斑驳的青石,仍在历史的书卷里述说着一语道不尽的丰盈与苍凉。
声明:本网转发此文章,旨在为读者提供更多信息资讯,所涉内容不构成投资、消费建议。文章事实如有疑问,请与有关方核实,文章观点非本网观点,仅供读者参考。